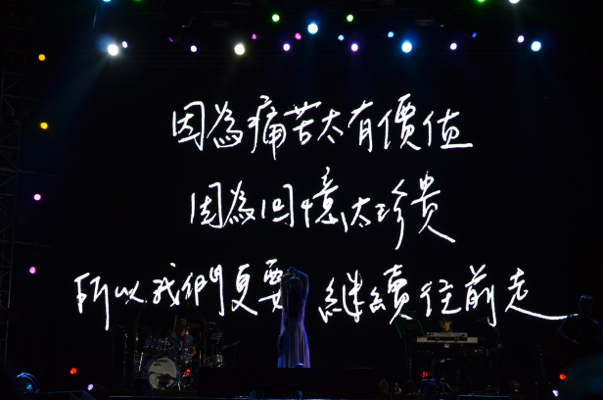
@wotan 可以确定是有红色资本支持。缅甸人哪有那么高的器官需求量?或者说缅甸人有几个人需要换器官、换的起器官?武汉是PRC最大的器官移植基地。北京开发的器官移植产业链,最早是是1989六月4日之后由于西方制裁,邓小平意识到外汇短缺但又需要维持既有在海外飞碟活动,去“突破北京的外交困局”,然后命中层康米去国际黑市找到的一条门路。这就和共产党在南泥湾种植鸦片一样,鸦片是很好的镇痛药,在战乱年代自然就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亩产收益)。
不过近几年国际器官黑市被国际警察打击的比较狠,所以PRC开发的这个产业链主要就给中国高层自用了。去年有个政协高层,好像和教育政策关系密切,死于武汉肺炎。有个中共干部写了篇悼文,其中说到:...鞠躬尽瘁,哪怕全身器官都换了遍,依旧坚守岗位,为共和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而武汉失踪大学生的新闻过去十年异常高发。武汉还有中共违约(和法国)自建的的世界最先进的生物实验室。
繼續昨天的話題。
昨天說到大家夥的吃飯問題並不需要一個人來專門解決。基本的發錢和市場經濟就足以保障每個人有飯吃,這不是什麼難事。難的是什麼,難的是經濟被阻斷。
去年是很多上海市民第一次嚐到餓肚子的滋味。不是他們沒錢,也不是糧食不足,而是有人堅持要把人都關起來導致的飢餓。上海是政府組織力量很強的地方,這次的災難足以證明,光靠政府組織是不足以讓人吃飽肚子的,解決吃飯問題還是要靠市場,他是我們真正的得力助手。
造成了這麼大的災害後,那個始作俑者還在一本正經的研究怎麼讓人不挨餓,真的是非常黑色幽默了。前陣子的確保耕地紅線的一地雞毛,就是典型的用一個錯誤去掩蓋另一個錯誤。
說了錯誤的例子,我們看看正確的作業是怎樣的,西方人沒有我們這麼拼命工作,他們憑什麼不擔心挨餓呢?
大流行中,西方主要經濟體幾乎都發了錢,為什麼要發錢?因為先進的管理經驗認為,如果人財物的流動一下子陷入停滯,就像人體內有了血栓,這時候部分肌體可能會由於供養不足而發生壞死。壞死後,哪怕消除了血栓,這部分肌體也難以起死回生。發錢就是為了保證個人和企業不會在這輪劫難中壞死,一旦大流行過去,整個社會就可以迅速恢復日常。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了,先進的社會管理使西方在大流行中並沒有中國這麼多的次生災害。在大流行結束後,上海的經驗表明,缺乏良好的呵護,則經濟停滯對個人和企業的傷害在災難過去後依然揮之不去。與此同時,西方大部分經濟體還是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最明顯的就是他們的失業率仍然維持在低位。
當然,我們都知道最近中國已經停止公佈失業率了,這個舉措能解決民族自信心不足的問題嗎?至少,我希望他能加深你對社會管理水平的認知。
to be continued
6月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1.3%,这个数据的达成还是建立在:农村户口的不统计(因为可以回家种田),每周工作至少1小时的算就业,在咸鱼上卖过东西的算就业,在自媒体平台发布作品的算就业等等,哪怕如此统计,每五个青年里也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而到8月份青年失业率更是不再公布了,也就是靠6月那样宽松的统计方法,也无法让青年失业数据变得好看起来。
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种“警惕身边的间谍”这样的宣传。毕竟在高层脑里,谈失业率必联系到颜色革命,突尼斯颜色革命时期,估计有30%左右的年轻人无法就业。法国西班牙等国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之时,同样发生不少上街游行示威的活动。显然中共高层最害怕的,就是青年失业率数字触发颜色革命,就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开始聚集在街头,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他们越是宣传要抓间谍,抓境外势力,我们就越知道青少年就业形势严峻,也就越知道他们其实也在担心受怕,害怕自己同历史上那些独裁者一样,受到革命的审判。
转发:六集纪录片《陌生人》预告片
2017年,因为我先生的工作,我们全家迁往西班牙巴塞罗那。离开北京前,我把所有以前采访穿过的西装都送了人。对我来说,这是个解甲归田的动作,我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工作,只是生活。我们住到了人流密集的兰布拉大道边上,它代表我想要的游客式的生活:与人互不相交,各行其是。
一个月后恐怖袭击发生,打破了这种幻觉。就在兰布拉大道上,22岁的袭击者驾驶货车,以Z字形冲了800米,撞击一百多人。他不可能看不到女人和孩子,听不到尖叫和人落在挡风玻璃上的声音,但他停下车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车底盘下的人太多,无法再往前开。
兰布拉是我先生回家的必经之地,恐怖袭击发生时我有十五分钟联系不上他,紧张感攥紧我头皮可以把我拎起来,脚底的汗却把我粘在地板上。
当晚巴塞罗那从没那么寂静过。我女儿睡得很不安,小手指轻轻抽动。我握着它,一边看新闻。凌晨时我从床上弹坐起来,手机短讯说:新的袭击发生。五人拿着刀斧砍向路人。我推醒我先生,他脸上像痛苦也像悲惨的笑,那是荒诞的表情。他说“不可能吧。”
这一天还没过完,至少十四人死了,130多人受伤。
第二天我们走上兰布拉时,让我震惊的不是看见了什么,而是什么都没看见。这条欧洲最繁华的步行街上空空荡荡,连鸽子都消失了。遇难者存在过的唯一痕迹是地上画着的绿圈,其中之一代表三岁的男孩哈维,和我女儿一个年纪。我先生半蹲在地上看那个绿圈,如果当天稍早几分钟,他也会在这条街上,戴着耳机,扛着沉重的箱子,那辆车如果从身后来,他会什么都听不到,也无法闪躲。
五天后我带父母去法国旅行,我们打算去的每个景点在过去一年里都发生了袭击,这个世界到了在镂空的埃菲尔铁塔周围建起防弹墙的地步。回到西班牙,我们想搬去海边小镇Salou生活,但去了才知道我们住的宾馆是本拉登的特使与911劫机犯会面的地方。我进入那个512房间,阳台上两把椅子正对着暗黑的天井,他们会面的目的是确定袭击目标,七周后飞机撞向了双子塔。
恐怖主义在欧洲扎根之深,之广,之早,远超我想象。
最让我震惊的是袭击者的脸。如果在大街上遇到,我会认为他们是学生。他们攀岩,在沙滩吃烤鱼, 穿着法国足球队队服。没有一个人有恐怖主义前科,没人在海外受训,他们长大成人的地方没有种族冲突纪录,几乎没有失业人口。这些移民第二代比父辈更有语言、技能、有工作、受良好教育、更融入西方,恐怖主义为什么恰恰动员这一代?
没有答案。结果是一个社会被严重撕裂,我听到了阴谋论,看到了极右的崛起。全球范围内多数恐怖袭击遇难者是穆斯林,他们成了双重受害者。这是恐怖主义的真正目的:破坏社会结构,让邻人相互恐惧。
我想跟身边人谈谈我的困惑,因为我只知道恐怖分子不是什么,但他们是什么?但人们总说“谈恐怖分子他们就赢了,继续生活是最好的报复,把话语留给受害者。”
但受害者的家人无法继续生活。六个月里哈维父亲敲了每扇门去问儿子为什么而死,听到的只是沉默。他瘦了很多,胡须白了,看上去筋疲力尽,“什么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吗?一个死去的三岁男孩的父亲?我受过什么训练呢?”
他话里无助的愤慨刺痛了我。袭击者死了,支配他们的东西还活着,每个人都可能是它的受害者。我想知道的真相我应该自己去找,因为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
两个月之后,我开始这个片子的调查。
采访在五个国家进行,此前我几乎从未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同时还要处理大量西班牙语,法语,荷兰语,阿拉伯语的材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件事,如何完成,在哪里播出,这意味着它只能依靠个人资金,极小的团队和局促的制作条件。在漫长的五年中,这件事不只是我的工作,也成了我的生活。很多夜晚,在离家万里的大陆上,从稿子中抬头,看到明月广照大地,我找到我的归属。
今天这个六集纪录片和一本书完成了。片子将在8月17日播出。如果能我会发在这里,如果不能,请移步Youtube账号@chaijing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