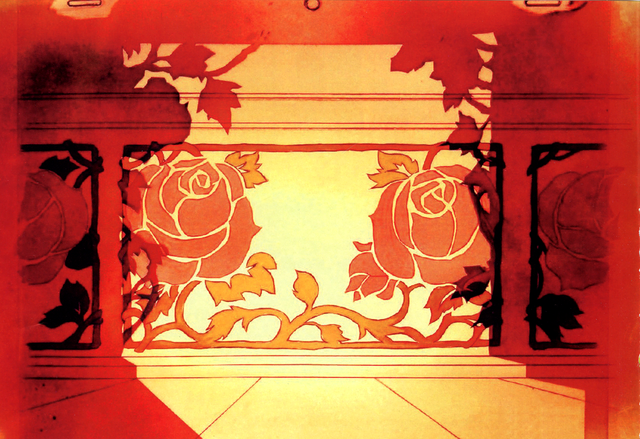
Aeon上个月的一篇关于mental disorder的文章昨天读觉得对于这几天过于热的抑郁症讨论非常有启发。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了既使是来自医生的系统化的诊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在当下的体系中,诊断不像声称的那样完全是“中立”、“客观”的descriptive,而且是prescriptive——“患者”在被确诊的同时也被推上一条狭窄的预设好的“治愈之路”,“想被‘治愈’”的道德义务要求ta必须合作,而“患者”的身份在给予ta一些医疗资源的同时部分剥夺了ta的完整主体性(科学/专家权力凌驾于ta本人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
日本的一些mental disorder人士由此发起了一个名为tōjisha-kenkyū的不同尝试。他们既是“患者”,又是观察/研究自己的“专家/研究者”。而且就像科研领域的peer-review一样,他们彼此分享自己的认知,对比发现自己理论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共同“生产”/produce对一种疾病的集体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并且这个过程也锻炼着他们的表达交流能力和自信,帮助他们更清晰要求社会如何去适应他们的存在(而非强迫他们“以健全人为标准去治愈”以适应社会)。另外,有着第一手症状体验且长于交流的他们还可以比“健全人”医生护士更能和其他不同疾病但有相似症状的患者沟通并带去慰藉。
我觉得tōjisha-kenkyū这个尝试具有某种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气质。“研究者/专家”和“患者”之间没有固定的区分,而是同一个人身上流动/多重的状态,这让一个人的integrity得以保全。“专家/患者”们的peer-review式交流不仅是collective的知识生产(不是少数人的专有),也承认了知识的perspective(而非descriptive)。个体的体验和认知得到尊重,避免了科学的暴政/tyranny of science (个体的经验可能是普适的也可能是独特的,还可能是两者的混合)。并且,“健全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Aeon | Tōjisha-kenkyū
https://aeon.co/essays/japans-radical-alternative-to-psychiatric-diagnosis
(我不懂日语,很好奇tōjisha的具体意思,文章里有英语翻译,但觉得解释得不够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