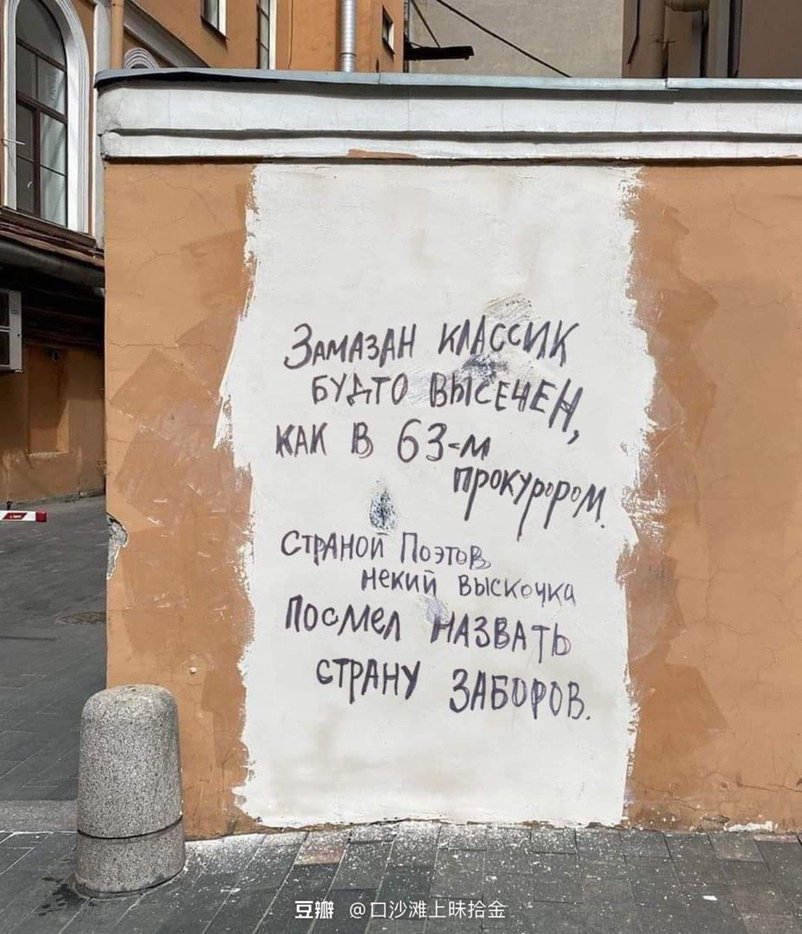
春山潮汐
转嘟
看了《人物》写戴锦华的文章,就觉得吧,戴着镣铐真的没法跳舞。复杂微妙的问题,有话直说都不一定说得清楚,如果处处受限制,时时要留意回避房间里的大象,就更是不知道在说啥了。比如里面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经过漫长的反抗之后,只有性别议题硕果仅存?”但是后面接了句什么呢?接了句“所有的反抗必须是建构性的”。我理解这里面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在所有的反抗中,性别议题是唯一能够在审查中找到夹缝,从而至少是部分存活下来的。因此,性别议题如果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反对上,就太单薄了。它应该对自身处境有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做一些整体性和建构性的工作。”当然,我也许是自作多情,也许作者根本没这个意思,纯粹就是把两句没什么关系的话放在一起。但是谁也不可能知道了,因为谁都知道“性别议题是唯一能够在审查中找到夹缝的”这句话,是不可能过审的。以上只是一个小例子,整个文章充满了这种不知所云的拼接和破碎感。有些地方,我大致知道中间缺了些什么,有些地方,我脑补都补不出来,只能当成是作者自己也没想清楚。而就是因为审查的存在,导致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哪里是意有所指,哪里是自己也没想清楚。审查之所以会使整个民族越来越笨,就是因为在这些最需要精密的地方,不准许完整充分地呈现思路。久而久之,人们就分不清隐喻和糊涂,分不清暗示和混乱,从不清聪明和愚蠢。当然,还是会有聪明人存在,但他们只是在世侩的意义上越来越精明,而在智识的意义上,确实是越来越蠢的。鲁迅说当看中国人的书,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成立。因为这种体制性的愚蠢,是没有人逃得过的。
春山潮汐
转嘟
- 我爱
- 自由的风
- 请
- give me a hug
生活在陆地上的海牛。
加入于 2022年0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