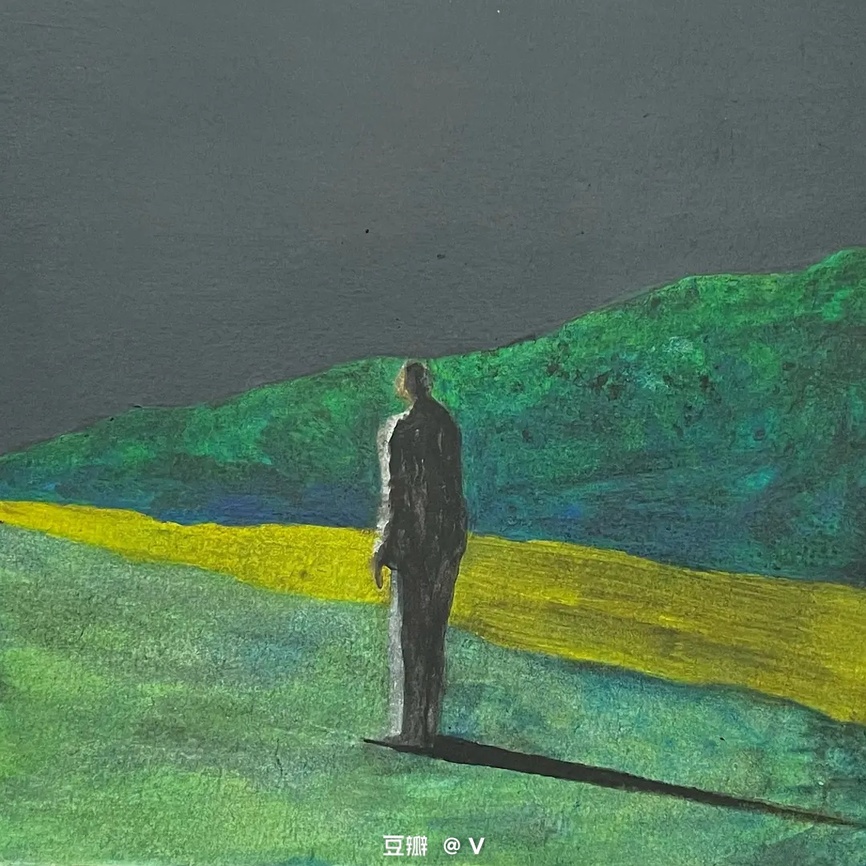
经过一座废弃的旧屋时,斑驳的墙壁印着几行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是伟人语录择了出来作了宣传标语,也是时代荒唐的一角。一旦作了意识形态的口号,这句话在原文具体的语境所表示本身的含义也就失去了。所以当它被搬用时,其所预设的性质变得单一,本身的逻辑也不容推敲。而它隐含的角色酷肖二元叙事的剧本,具有极度理想化的自恋情结。在这种话语充斥的官方意识形态中,自我反思与纠错的机制更多地也是表现成一种表演的姿态。
#末日遗绪
“(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存的一点民族自尊感,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部分地区与少数族群聚居地的分离主义隐患,以及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所有所谓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等。
(官方)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同时,)让众人在一片喝彩叫骂声中忘却自己作为国家奴才的屈辱身份,甚或在面对某个弱国(或弱势族群)的强硬姿态中找回一点做主人的快感。
在一个权力压倒一切的国家,道德堕落是迟早发生的必然结局。这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和道德无关,掌握权力尤其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权力的事实本身不等于善恶或对错
但是,一旦权力成为一种社会通货,不仅可以兑换金钱、文凭、荣誉、美色,而且成为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来源,社会就丧失了基本的是非观念······”
节选《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
宿雨而白日放晴,这算是顶好的时节。偶尔回想黄锦树的《雨》或者是阿彼察邦的《幻梦墓园》,会觉得有一种分外的亲近感;最近看电影时常坠入梦河,醒转时重看。
夜以继日或是日以作夜,人生就如此无声逝去。
存在感有时意味着异端,一种对如常的反对。
#昨日遗书
最近找来看了王德威关于抒情传统的反叛的视频。抒情传统的发章自诗学的创作,“诗言志,词言志”一说便是表明创作源于作者的本心的,而这是有着悠远的传统的。但作品与作者是否真的具有同一性,这是越来越被人重视并质疑的。
人只是人。
其实这是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我自然是很乐意息交绝游、静默自处的,但有时也会疑虑这样的方式。可是心底还是存着几分惧意,乐趣几多并不是我要追求。
在陈奕迅的《THE KEY》中由林夕作词的《任你行》。
“为何在雨伞外独行,
亲爱的 等遍所有绿灯
还是让自己疯一下要紧
马路戏院商店天空海阔 任你行
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
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尘
原来神仙鱼横渡大海会断魂
听不到世人爱听的福音
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
无人理睬如何求生
顽童大了没那么笨
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
然后同沐浴温泉
为何在赤地上独行
顽童大了别再追问
可以任我走
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
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十日谈
昨晚落雨只落了几个时辰
这可以解释为某地某时局部有雨
我想这片土地到底是如此广大
以至于可以分成两块大洲
而这雨只是恰好经过
今天的新闻报道某地某时某人犯罪
我们心在那一刻变得如此细薄
以至于人可以拆成两半
这人或许是恰好翻牌
我们的坏运气到底要靠谁来用光
我们的好日子到底是被谁来度过
我的眼只能看见局部
我的耳只能听见局部
我有时也可以成为这局部
这局部的一模一样的一员
公义或许恰好成为这局部
幸福也是
不幸也是
快乐也是
悲伤也是
可是到底要多少个局部才能凑成我们的生活
#末日遗绪
当苦水当成笑料,生活里的甜蜜早已罕有得需分外珍惜。无事之年的福报只能一信再信,阿弥陀佛。
这世间的黑暗让你心暗一层,再暗一层。知道的是圈内,不知的是圈外。
今宵的笑话再尽兴一点。
矛盾一些,无知一些,世故一些,愚蠢一些,再老去一些。
#末日遗绪
以为失去的仅仅是勇气,其实是良知;回避不是办法,回避不是办法,回避不是办法;病症的治理,不应止于康复;旧时代的大山被推翻了,可山外有山。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我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免疫学家来到这个国家的。我选择这个领域--如果不考虑想要离开中国的理由和拥有谋生技能的实际动机的话--是因为我喜欢免疫系统的工作概念。它的工作是检测和攻击非自身;它有记忆,有些记忆像生命一样长久;它的记忆可以有选择地出错,或者更糟糕的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出错,导致该系统误认为自己是外来的,是需要消除的东西。immune(来自拉丁文immunis,in- + munia,服务,义务)这个词是我最喜欢的英语语言之一,拥有对疾病、对愚蠢、对爱和孤独、对麻烦的想法和无法缓解的痛苦的免疫力--这是我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所期望的特征,同时也知道这种愿望的徒劳。只有无生命的人才能对生命有免疫力。"
尚在阅读李翊云的《Dear Friend,from My Life I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
我英文不佳,辅以deepl来勉力而读。
李翊云是拒绝将自己的著作译为中文。个中原因在阅读时就能深切明了。一个如此坦诚到令人心碎的地步的人。
#抄书匠
谈列车。
黄伟文执笔写下的《亲爱的玛嘉烈》,不论是黄耀明演唱或是林宥嘉演唱的版本,都各有风味。应该是最喜欢的一首列车行歌。
“惨绿青年
你短发密且软
谁给你剪
谁给你剪
如你出走那一天 没人看见
••••••
诚心祝福你 捱得到 新天地”
末句作赠句最宜。当我写文字时意识到,称己消极黯淡,祈愿旁人光明乐观。我总是对于那些值得深信的总是怀疑,写给他人却希求对于那些失望的还要寄望。自己观点总是不明朗,而苛求别人保持一致。《善的脆弱性》我需看。
《爱在黎明破晓时》(1995)与《甜蜜蜜》(1996)是同车旅客。爱情与奇遇勾连,机运虽有,无关合理。如在心尖,无问解签。
《热情似火》(1959)与《你逃我也逃》(1942)是幽默闹剧。政治戏讽或社会嘲弄产生的笑声里咀嚼时是泪水涟涟、恶意滔滔,滑稽时胆寒,出丑时心凉。权威与暴力,笑笑就冇了。
《薄荷糖》(1999)与《复仇在我》(1979)是谋杀青年。恶是如何诞生的,答案在风中飘扬。
《双重赔偿》(1944)与《红圈》(1970)是钱财恶事。流亡与谋杀的戏码百听不厌,黑暗里的灯晃眼,罪恶里的情动人。社会奇闻,在你也在我。
#十日谈
这长路极渴睡的我:耳朵轮替Chet Baker的愚人恋曲、腰乐队的失意情歌;眼目交给《一一》,虽衬趣,而电波尚远。脑际响起短句:今日晴转阴,而我阴转阳。
归乡雨途燥焖,家屋潮迹斑斑。
《时代革命》:每一滴泪珠都有你的尊严,你所展露的勇气,我羞愧难言,悔恨之前我所有的刻薄与无知。
“怕什么?又不会被抓走。我们犯了什么罪吗?”
“为什么没有罪?赖活着就是吃苦受罪。”
••••••
“你打算逃到什么时候?你现在也三十多了,不再是大学生了。你又不可能一直逃到世道改变……你该不是相信世道会发生改变吧?”
“大哥,世道是否改变并不重要。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认为正确就一定要做吗?”
“如果一件事是正确的,世界上总要有人讲出来吧?”
《鹿川有许多粪》李沧东
#抄书匠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最喜欢的一版就是收录在巴奈《勇士与稻穗》的翻唱。巴奈的口白增色太多,那种对他人理解关怀与对爱情的犹疑百转使歌曲诠释出更丰富的意蕴与情绪。答案并不重要,若真的值得,又有何不可。可是值得,往往是后验的。
“喜怒哀乐/有我来重蹈你覆辙”
林若宁讲这首与《背影》是两生花。
“不响一声/常在你左右共鸣”
蓝小邪写过《你快乐未必我快乐》收录在田馥甄的《渺小》。
“我的眉头/难道铺满你美丽叹息/才能参透悲伤和欢喜”
尾句讲的很明白了,“你爱你所以我得爱我”。
我将诚恳视为一种美德。虽发乎于心,但不拘于礼的。礼节性言谈举止固然热络,也有讨好之嫌。但我并不排斥,仪式固然可有可无,但也可表征人心的反响抑或平添稳定之意。真挚虽动人,但真假难辨。迷信文字艺术的人,常自认为于言语中能识破一个人,面对巧言令色的人,就易跳入其编织的牢笼。
对于热情,在还没丧失它的时候。你还可以去生活,去拥抱一切尚未降临的痛苦。
我爱静默,爱深沉地思考。说教是一种基于价值观地品头论足、生硬地将自己的观点架构在别人的人生中。但自己往往很难去界定那暴力的红线,甚至是不自知的。关于共情能力,我常自省于是否缺乏一种对于他者的痛苦、他者的境地、他人的感受的想象力,反之,这是否是一种廉价的自我感动,以此自欺未沦为麻木的躯壳。真正我所知的是我自己的痛苦。我并不否定理解,我只是怀疑这理解的深度与面向。我们更需要一种社会性的理解,这不仅需要尚缺乏的常识以及对少数人的重新定义与认同。
我是讨厌与人接触的。这种讨厌的根源是对自身的鄙视与厌恶。相较于悦纳自己,我只是冷眼视之。好人,这一称谓是极具讽刺性的谎言。常年在道德的思考与自困:道德是一种社会性的概念,是基于他人的并与他人联系的。自我表演与迷恋是我厌嫌的。若只是基于一种良好的动机,不审慎地看待行动的影响,而视其作为善的代价,亦同样是恶,虚伪的恶。
我讨厌虚伪。但不得不认识到与虚伪相对的是赤裸,不断怀疑我真的有勇气去展露赤条条。不设防的人易露出天生的脆弱,遮掩与否,它都存在。在一个甚至宣言成丛林的世界,暴露是近乎一种自毁。人不得不有限地去交游于深知中袒露。人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游走。
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贡布斯写道,“那些真诚热爱自由却将无限权力授予人民主权的人们,他们的错误产生于他们的政治观念的形成方式。他们注意到历史上有过一小部分人、甚至某个个人掌握巨大权力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但他们愤怒地反对的是权力的掌握者,而不是权力本身。他们只想取代它而不是毁灭它。它过去是个祸根,但他们还是把它看作一种征服。他们把它授予整个社会。它必然从全社会转给大多数人,又从大多数人那里落入极少数人、经常是一个人的手中。它产生的罪恶和从前产生的罪恶一样多;于是,各种事例、缺陷、理由和证据会层出不穷地出来反对所有的政治制度。”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弱权力、甚至反权力的。
同理而言,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恶的本身。在如今性别议题不断重申的时代。人与恶的关系被倒置了。各个群体彼此攻讦,有的爱倒污名的脏水。
是偏见吗?是制度问题?是结构问题?是性别本身?是生理问题?是教育问题?......
无论是《德伯家的苔丝》还是《无名的裘德》,主人公无论思想如何进步,最后为何仍陷入如宿命般的悲剧中?
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无欲无求,退避到最低层次的生活的角落。如何让每一个合乎人性选择变得轻盈?
如果我真的有够命,活到新世纪,下个世纪的孩子也会经历一样的幻灭吧;自恋与自厌并存的人,并不稀奇吧,讨厌自己的一切,却不时又为此沾沾自喜;母语、故乡、终年的雨--流亡会是悲剧的答案抑或另一场悲剧的车票?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