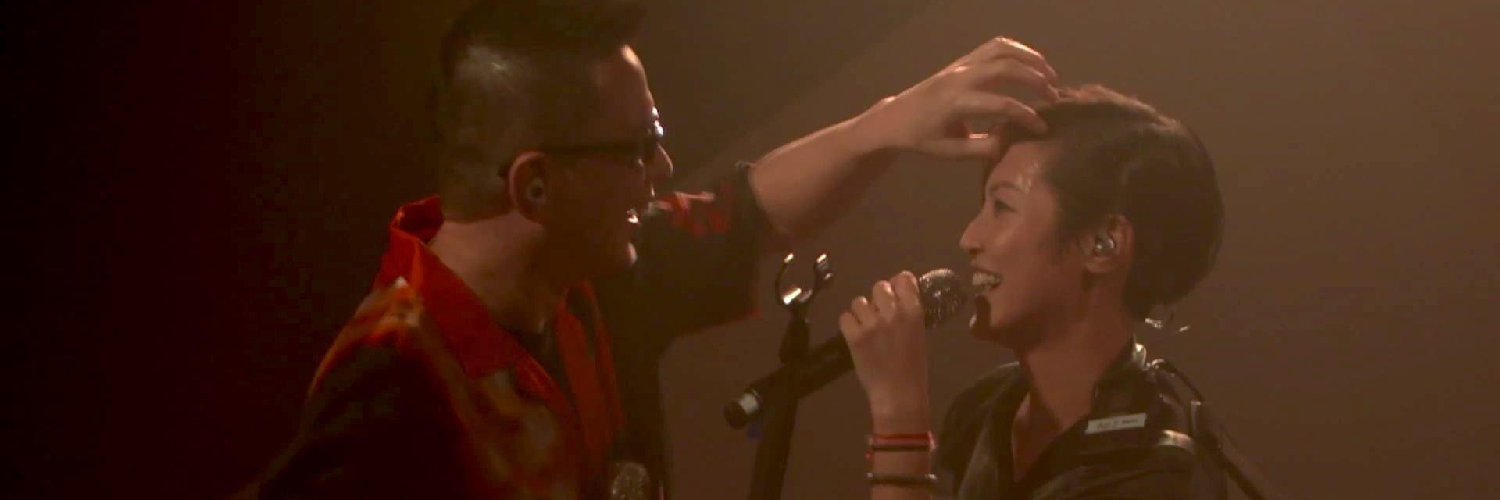
【帮助别人解决心理问题竟成“举报” 大学“心理干预”系统为何越来越像“监视”系统?】李舜(化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试图帮助别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行为,竟成了“举报”。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在某社交平台上偶然看到一个女孩匿名发求助帖:“想自杀。”看到这句话,主修心理学的李舜,本能地感到一丝不妙。他装作同样想“自杀”的学生在帖子底下留言:“我也想自杀,要不聊聊?”没过多久,李舜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好。”女孩简短地回复道,同时私聊他了一个联系方式。
女孩是一位国内名校的大学生,没经历过创伤性事件,但因为抑郁症导致情绪低落,悲观厌世,也没有动力就医服药。这是归国不久的李舜第一次面对与他专业高度相关的求助样本。他准备将自己从国外大学里学习到的经验应用到女孩身上。 “一般高校都会有成熟的心理干预流程,”李舜回复女孩。“比如,带你看病、学业减免、每周1~2次免费心理咨询等。”
这是李舜在国外生活中了解到的经验。李舜问女孩,是否愿意让他代替她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汇报,帮她“对接资源”?女孩同意了,并把自己的学生证发给了他。李舜照着学生证上的信息打电话给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了,你还挺有爱心的。”电话那头的老师夸他道,“我们会去核实一下。”
但随后,女孩质问他到底在跟谁“汇报情况”:“大半夜的,怎么学校保卫处来了两拨人找我?”原来,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将事情告诉了保卫处,保卫处立即把女孩的情况报告给了学办主任,学办主任又通知了辅导员。第二天早上,女孩告诉李舜,辅导员不仅跟她室友“核实情况”,同时还联系了她的家长。辅导员把学校的条例列出来,告诉他们不建议让女孩继续上学,“让我出去就医,如果就医后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就建议休学。”李舜一头雾水……学办主任是谁?为什么通知的不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为什么要和室友核实情况?
李舜很自责。他将事件的经过告诉了几个朋友,结果“没一个人说我做得对”。他清晰地记得,有位朋友甚至直接跟他说:“你这不是向学校举报她得了抑郁症吗?”后来,李舜从女孩处得知,经与学校协商,通过“家长陪读”的方式继续留在学校里上学。李舜意识到,自己成了让事态失控的“始作俑者”。但他也很疑惑,“为什么学校没有遵守心理干预最基本的隐私保护原则?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不该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这件事?”
高校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在一些大学生眼里,这个本意是“帮助”的系统,如今却越来越像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这双“眼睛”涵盖了“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四层“预警系统”。从开学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它似乎就注视每一个“状况异常”的学生,关注着他们的情绪、变故、挫折。等达到某一阈值,有的大学甚至会向学生发出警报:“你的情绪一直不太好,是否该考虑休学了?”有学生问:在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一位高校心理健康系统中的负责人员说,学校不是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而是帮助学生度过校内生活。“只要确认这个人不出事,危机就解除了。”(八点健闻)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 https://mp.weixin.qq.com/s/IfiLNdadl4YyTvm4Phv2jg
https://mp.weixin.qq.com/s/IfiLNdadl4YyTvm4Phv2jg
转帖:中国的零工体力劳动者到底有多被压榨——劝退贴——盒马分拣-蜜雪冰城经历分享——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楼主是去年毕业的某211硕士,以前没怎么干过体力劳动,出于对脑力劳动的“背叛”,我决定去找一个体力活儿干干,于是我伪造了高中毕业的学历,在2月底经由一个人力资源公司到了上海的一家盒马生鲜干分拣。
分拣场所是在一个灯光暗淡的仓库之中,计件工资,按照“合流”和“一体化”两种计价方式,所谓的合流就是在捡好货物之后不需要自己打包的,一体化则需要自己拿个箱子打包,合流的一件商品2毛五,一体化的一单是1块2,这个“一件”商品不是真的一件商品,而是同一个商品,比如有人买了五瓶矿泉水,这五瓶矿泉水算一件,而一体化,无论你拣了多少商品都是1块2,一体化的一单平均要有10件商品左右,而且还要自己打包,所以拣货员不喜欢干一体化的,但是没法拒绝,被派到什么单就是什么单。
拣货员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捡完货物,一般10件商品会给2-3分钟的时间,你需要在这2-3分钟的时间内,用手挎着提包,在面积大约600-700平米且构造复杂的仓库里,用一个扫描枪把商品塞进包里,然后拿着包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点,一旦超时就会被扣钱。与此同时,在工人们奔跑的另一边,三个管理员(两女一男)在椅子上拿着大喇叭不停地催促人跑快点:
“XXX!你干嘛呢!!磨磨唧唧的!“
”跑快点!都给我跑起来!”
“跑这么慢,还想不想干了?不想干就滚!”
你一边需要忍受管理员的呵斥,一边要像被鞭子鞭打的牛一样干活,是的,这是真的牛马,在这里,你不会有任何的尊严,任何的一点小失误都会遭受严厉的呵斥,我每天要听到十几句“草你xx”,甚至没什么失误也会遭到打击,有一次,一个分拣员好像跟一个女的管理员发生了争执,然后另一个女生过去看发生了什么(这个女孩还没有18岁,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在这里干分拣),然后那个女管理员看她走过来,就骂她:“滚回去!给你脸了?!看什么看!”,我还听到女管理员这样喃喃自语:“我最近是不是骂的少了,好些人干活不勤快,蹬鼻子上脸了!”
紧张而单调的劳动并不让我感到难受,顶多让我感觉到了一些人在劳动中的异化(实际上从研究的目的看,我并不排斥感受这种异化),但是那种充满了威权、严酷的工作环境却让我疲倦,以及内心深深的悲哀——我是学习心理咨询的,我的价值导向大体上是助人的,我并非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冷漠、防御、虚伪、暴力(事实上我在家庭和学校中也体会了不少),但是这种黑色的东西以一种大规模系统性的方式展示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心理学拯救个人是有可能的,但是拯救社会却是妄想,而从和分拣员同事的交谈中,我在看到力量的同时也看到了底层人民相比于其他阶层更多的迷茫——在这里,没有什么阶级上升/个人发展的太多可能,个人更多地只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或者压根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思考这些问题会让人焦虑。
金钱和权力的耦合让社会好像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扭曲状态,我在所谓的大厂也工作过,一边是阿里巴巴炫目的写字楼,一边和其旗下公司(盒马)处于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大厂的繁华之下不过是满地的虱子。
全文未完,全文见以下两个链接
原贴地址: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86078835/
备份地址:https://archive.md/Pq3JM
#schreiben读书笔记
或者说越来越觉得到表达观点,让观点可信/可靠,需要严谨的资料/数据支撑,我并没有对哪件事有如此渊博的了解。而且我的生活里现在充满了我不熟悉的事物,连下断言都成为一件难事 ![]() 当我试图理解荷兰农民的罢工,当我想不明白环境保护者抵制一家企业文化还挺不错的石油公司、当我真的见到了无家可归者——我不懂他们,我不明白该怎么解读,我以我的经验知道主流且简化的立场是怎么样,但我对这个社会不熟悉,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
当我试图理解荷兰农民的罢工,当我想不明白环境保护者抵制一家企业文化还挺不错的石油公司、当我真的见到了无家可归者——我不懂他们,我不明白该怎么解读,我以我的经验知道主流且简化的立场是怎么样,但我对这个社会不熟悉,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 感觉等过几年需要读一个社科的学位呢(
感觉等过几年需要读一个社科的学位呢(
- 勇敢的人
- 祝你在乱流下平安
- 声明
- 本人一切Po禁止转出长毛象/回关随缘/无原创嘟文不回关
- 梦想
- 和猫一生一世,死后上任天堂
会有很多猫猫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