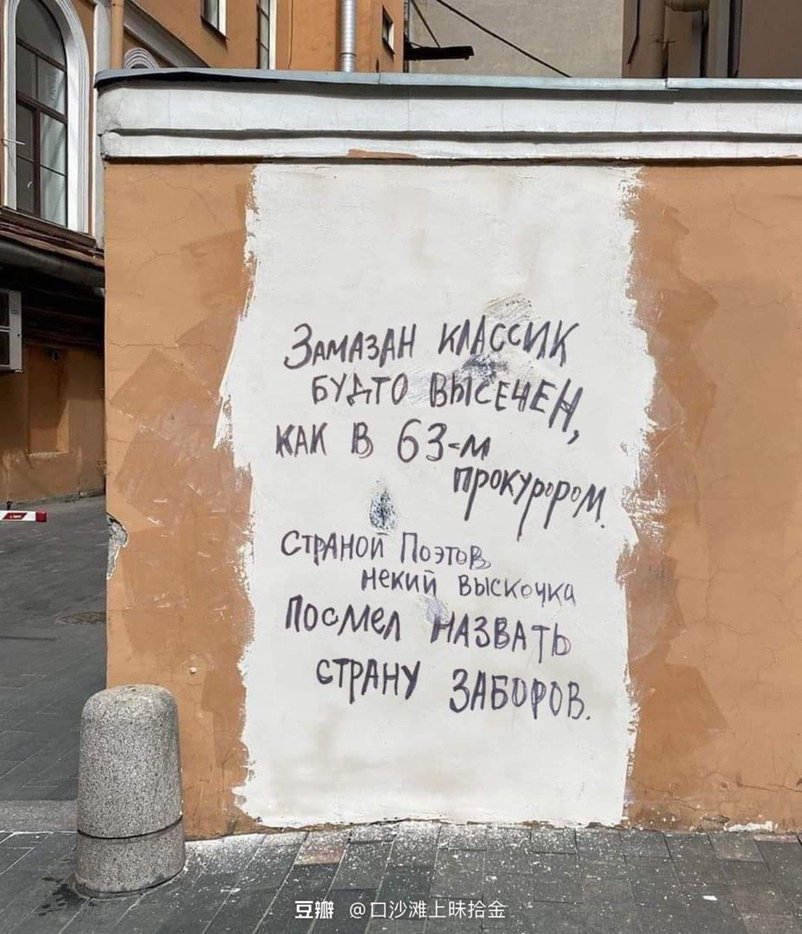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虽然听起来很绝望,甚至有奴性的味道,但其实在中式恐怖的语境里,是具有反抗意味的,而且是一种针对性的,根本性的反抗。因为中式恐怖有个特点(特别是跟俄式相比),就是以绵密、彻底、软硬兼施的压力,使受害者(由于压倒性的痛苦和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而合理化自己受到的伤害)成为合谋,从而达到完全彻底的征服。相比于肉体毁灭,这才是他们所追求的完胜——如果你不自杀,你就会自动变成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你自杀,你就会以拒绝改造的反面教材的方式成为系统的一部分。但是这里有个bug,那就是“咬着牙活下去”。关键是这个“咬牙”的态度——虽然不服气也不能怎样,但是怎样你都不服气,是不是他们也拿你没办法?只是要注意,时刻提醒自己处于“像牲口一样”的状态,当你拿自己当人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一切其实具有某种更高层次的合理性时,你就输了。
心态崩了,记录一下上海这段我家的经历。
我家五口人都是青壮年男女,四个还是学生,一个工作中。家里人多,又常招待朋友,平时就有多买东西的习惯,有一个冰柜,两个冰箱。几个人都比较反贼属性,上海刚开始感觉不好,就把家里的动物送到其他城市有朋友照顾,所以也很早开始囤货。新鲜食品、副食饮料,烟酒糖茶,各种品类都买了。也一直参加团购、抢菜。物资我们小区一开始有收到不少。但因为一栋楼前段时候有阳性,物资就开始不行,买东西的难度也很大。我们吃饭吃的良心不安,商量了一下,开始把一些新鲜食物送给需要的邻居,比如家里有小孩、孕妇、老人的。邻居们需求量不小,四天就清空了大冰箱。这两天开始彻底买不到东西,小区内陆续阳性,解除遥遥无期。我们商量一下就决定不再分东西给邻居了,自己也开始一天吃一顿,希望减少食物的消耗,多撑一段。虽然很凡尔赛的能吃饱也有零食。我们这栋楼离其他的楼有一定距离,相对安全,户型也比其他楼大不少,疫情一开始有人对我们这栋楼做核酸都是最后才来、物资都是先发,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家就被骂了,我们这栋的点名到我们家有食物不分给大家,说我们恶毒,其他栋就有骂我们这一楼的,也有说我们早早买东西,他们才买不到。很难听,一个群杂七杂八骂了一个多小时才算了。我很受冲击,象上友友们有来安慰我,心情舒缓了一些。刚才发现我家大门被人用口红写了骂人的话,一开始是我起头把食物分人,心态崩了。躲在房间里一边哭一边记下来。
当双语个体用两种语言做同一套人格测试时,他们甚至会表现出不同的人格,正如滑铁卢大学的一些在中国出生的双语学生在用英语或汉语描述自己时所发生的那样(Dinges & Hull,1992;Ross et al.,2002)。
当用英语来进行自我描述时,他们简直就是典型的加拿大人:他们大都表达出积极的自我陈述和心境;而用汉语回答时,他们给出了典型的中国人的自我描述:言谈中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那些符合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观念,积极和消极的自述与心境几乎各占一半。
当双文化、双语的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在与英语和西班牙语相关的两种文化框架之间转换时,也出现了类似的人格变化(Ramírez-Esparza et al.,2006)。
捷克谚语说,“学习一门新语言,就得到了一个新灵魂。”
摘录来自
心理学导论
戴维•迈尔斯
@reading
很反感“支那猪”“支人”这种群体化的侮辱性词汇,不管怎样它们在我这里都不可以被合理化。
我们和我们所厌恶的那些人的本质区别,不应该是抽象的政治理念,而应该是我们更能够在抽象的群体之下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人、重视每一份不公与苦难,能够不被偏见所左右而更自由地思考。这种群体化歧视和侮辱的词汇,在我眼中正是我们所厌恶的事物和人身上的粗暴和偏见的具体化。
这种词语的攻击范围是广泛而且暧昧的,该做到怎么样才不是“支人”呢?“如果这个词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从身心到灵魂都是个支那猪” 那么你又是为何觉得自己不是支那猪、自己从精神上脱支脱得比我更干净呢?毕竟在最原本使用这个词来对中国人进行广泛侮辱的外国人来看,用中文打出这句话、长着亚裔面孔的你,并不比我更不“支那猪”一点。
- 我爱
- 自由的风
- 请
- give me a hug
生活在陆地上的海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