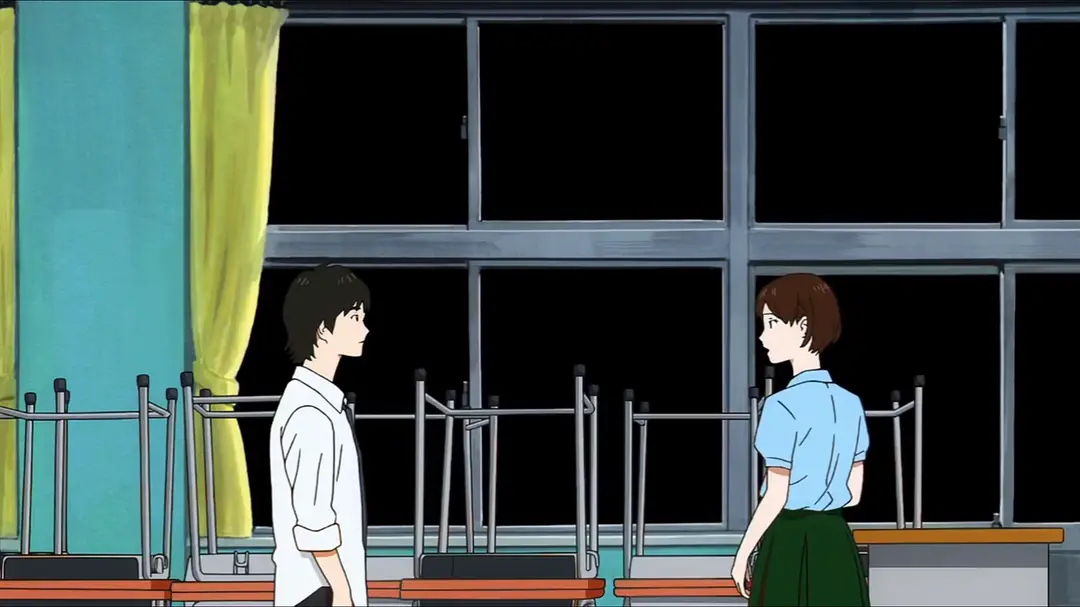
@Chord 什么这是!
@CDTChinese 好苦
“清零”以来各种嘲讽调侃,但几乎所有抖机灵的段子都充斥着恶心的性暗示。像昨天跟朋友聊起,说你国像个大型强奸现场,本以为奥密克戎是根假屌,当笑话看看,谁知假的用起来原来更可怕,你爹拿着艹你把你折腾死了,他自己可一点感觉都没有,不是假的哪有这种持久力?
比喻确实贴切,但一字一句难掩恶臭的厌女气息。不禁怀疑除了这种猥琐的荤段子,难道就没有别的形容吗?怎么说呢,好像还真没有。
你想,比喻玩梗本来就是借用夸张的喻依烘托荒谬的现实,但一旦喻依与现实过于相似反而没效果。
比如以前形容活得不成人形还能自嘲“牲口”,直到真的被囚禁、被打压、挨着饿、天天被检疫,再自比“牲口”就显得过于写实也就不痛不痒了。
说来说去就只剩女人。要知道在你国,一个城市再怎样被利维坦糟蹋,在欺凌的食物链底端依然还有女人。拿女性性暴行衬托自己的屈辱,永远不怕没效果,毕竟简中最极致最人神共愤的压迫,哪次不是体现在女性身上?
真正彰显利维坦“去人性化”暴虐的从来不是牲口,而是被父权反复蹂躏的女性。而当所有针砭时弊的梗不约而同指向女性,也许不只是厌女,而是人已经活得比牲口卑微了,除了自比女性还能说啥?
@juukun 笑死
@AFWood 真行哈
@Chord 呜呜呜 温柔头像让我以为我眼花了
看了《人物》写戴锦华的文章,就觉得吧,戴着镣铐真的没法跳舞。复杂微妙的问题,有话直说都不一定说得清楚,如果处处受限制,时时要留意回避房间里的大象,就更是不知道在说啥了。比如里面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经过漫长的反抗之后,只有性别议题硕果仅存?”但是后面接了句什么呢?接了句“所有的反抗必须是建构性的”。我理解这里面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在所有的反抗中,性别议题是唯一能够在审查中找到夹缝,从而至少是部分存活下来的。因此,性别议题如果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反对上,就太单薄了。它应该对自身处境有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做一些整体性和建构性的工作。”当然,我也许是自作多情,也许作者根本没这个意思,纯粹就是把两句没什么关系的话放在一起。但是谁也不可能知道了,因为谁都知道“性别议题是唯一能够在审查中找到夹缝的”这句话,是不可能过审的。以上只是一个小例子,整个文章充满了这种不知所云的拼接和破碎感。有些地方,我大致知道中间缺了些什么,有些地方,我脑补都补不出来,只能当成是作者自己也没想清楚。而就是因为审查的存在,导致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哪里是意有所指,哪里是自己也没想清楚。审查之所以会使整个民族越来越笨,就是因为在这些最需要精密的地方,不准许完整充分地呈现思路。久而久之,人们就分不清隐喻和糊涂,分不清暗示和混乱,从不清聪明和愚蠢。当然,还是会有聪明人存在,但他们只是在世侩的意义上越来越精明,而在智识的意义上,确实是越来越蠢的。鲁迅说当看中国人的书,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成立。因为这种体制性的愚蠢,是没有人逃得过的。
@eibon 想立马关注哈哈哈哈哈哈
@Chord 呜呜呜好可爱的画面
@hncdmdym 倒霉我西
@Chord 啊。。
简中互联网令人突发恶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