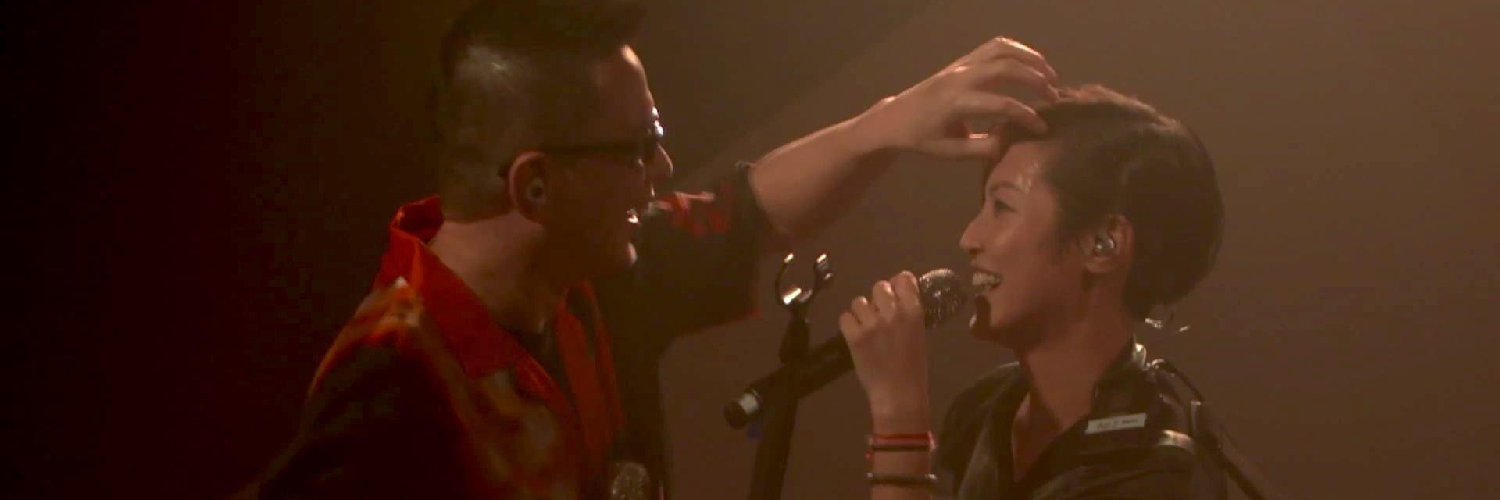
我出生以来所有受到的教育就是人要往上爬。但与之相对,虽然比起大多数中国人,我已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但我的学术训练烂到大四的时候,一篇2000字的英语小论文,我在很熟悉主题的情况下,前前后后要写十天,我没办法快速读文献,没办法独立做研究。我非常非常遗憾我没有受过很好的人文学术训练,今年吸收的知识已经超过过去四年的所有,可见本科的质量有多不入流。
我要拼命告诉我自己这不是我的错,而且我的目标不是成为学术达人,而是能顺利毕业找到工作留在异国。
在来荷兰以前,没有长辈像我房东那样跟我说,学习不是最要紧的,生活也很要紧。他们只会在我失败时展现失望,批评我如何懒惰如何蠢笨,或者在我拿出成绩后又一副“我没看错你”的样子,好像一切都来得很容易。高考失利的狼奶我吐了整整两年,那两年我是多么刻薄糟糕的人。有时候回想人生会觉得,我一点都不想重来,即便现在的我仍然不够好,但我已经花尽力气才变成一个“好人”。
妈的全宇宙
喜欢动作设计和剪辑调度,非常流畅,成本不高但很有趣味,杨紫琼打起来还是这么迷人。但这个结尾怎么会是东亚家庭和解的大俗套呢,东亚家庭根本不和解啊!东亚一般家庭:有本事你就走,我没有你这个女儿[怒骂]东亚开明家庭:只要你不搞同性恋,我们还是一家人[苦涩]所以别把美式套路栽赃到东亚家庭身上!我对片中母女关系没有特别的触动,在戏剧离奇的环境设置里,“let me go”的痛切被童真化了,它不叫自杀、自残、断绝关系,而叫奔向贝果宇宙,同时,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只能止步于生死分界线外直面自身痴愚和无力的母亲,被赋予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超能伟力,让她不必付出心碎的代价去看到家庭关系中最深重无解的那部分痛苦(不愧是心理咨询大国,深信语言沟通的力量,我老中还是觉得说谎与沉默更保护心理健康!),所以它并不是到结尾才和解的,而是一开始就定下不要过分拷问的基调,真正的刀枪过体的森凉还是得留在卧室床板下日夜东流,放在荧幕上恐怕无人乐意消受。说到这里想起讲移民生活的电影我很喜欢前年的米纳里,一对韩国夫妻在美国种菜创业的故事,可以看作妈的宇宙中一个现实切片,总是匮乏总是艰难的亚洲人深信相互亏欠的关系方能长久,那当然有痛苦,但这种痛苦里有很震撼我的决心,毕竟爱人与领受爱的离场,都不是只有快乐抱抱贴贴的事啊。既然是无论走到哪里方方面面都以勤勉奋发闻名的族群,自然这方面也一样。哎。
现代语言学描述而非评判地接受一切新兴的语言现象。半截入土的老人家痛斥新兴语言的庸俗,更多是痛斥语言不如他们所想的正统和优雅。但非正统的语言也有内在逻辑/语法。典型例子是美国黑人俚语,因为多缩写、省略被痛斥为不正统的英语,但他们有系统性的语法,被看低更多是因为此类语言与黑人身份挂钩。
流行语说明语言还是活着的,真正死掉的语言不会有新东西出现。君不见各大英语词典年年更新词库。
----
早些年我刚学到这点的时候也觉得如此,何必痛斥流行语,不过是欺负年轻人年轻,如同痛斥年轻人网络游戏成瘾,不够上进,痛斥网络文学低俗,痛斥韩流明星娘炮一般,在痛斥里找补自尊。结果现在的一些流行语魔怔到了我难以理解的地步(跑毒/投毒/大白/nmsl云云)。我放弃理解了,拒绝使用是我最后的倔强。
深夜吐槽一下那位guest。
我不喜欢他,倒不是他说的话不对。他说的一些观点不错,他甚至施舍地提了女性因为算法会筛简历的时候被筛掉,这点也没错。但他讨厌在:一,他用来作证观点的论据不是道听途说的鸡汤故事(也就是将复杂的事简化成“反直觉”/令人焦虑而适合传播的风格),就是吹嘘自己人生经历之丰富。他一个发达国家高学历白男,吃尽性别种族阶级学历红利的人说“学历不重要”。他论证“被人们认为重要的虚拟事物已经不具备价值”,说“我领英很多connection,但它们对我都没有用”。何等的傻逼才能大庭广众之下舔着脸吹嘘啊……没人关心你领英多少connection好嘛。林垚老师说不具有身份的人可以发言,但是要多学习,去补足经验的不足。这样谦虚的人世界上有多少呢。二,他试图把企业家画大饼的风格带进学术课堂,完全临场发挥的样子。开头问:“你们想知道什么有关我的事情?”(……)隐隐还看不起我那很认真帮他串逻辑的教授。我的教授提问,他超级没礼貌:“你没听懂我的话。”三,他走马观花提到很多事情,讲性产业,讲贩毒产业,好像很有思想、很酷的样子,但是每一点都没有很深入的分析。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人很混得开。
- 勇敢的人
- 祝你在乱流下平安
- 声明
- 本人一切Po禁止转出长毛象/回关随缘/无原创嘟文不回关
- 梦想
- 和猫一生一世,死后上任天堂
会有很多猫猫日常
